内容详情
2025年09月05日
母亲的名字镌刻在红色记忆里
阅读数:555 本文字数:3294
□ 沈月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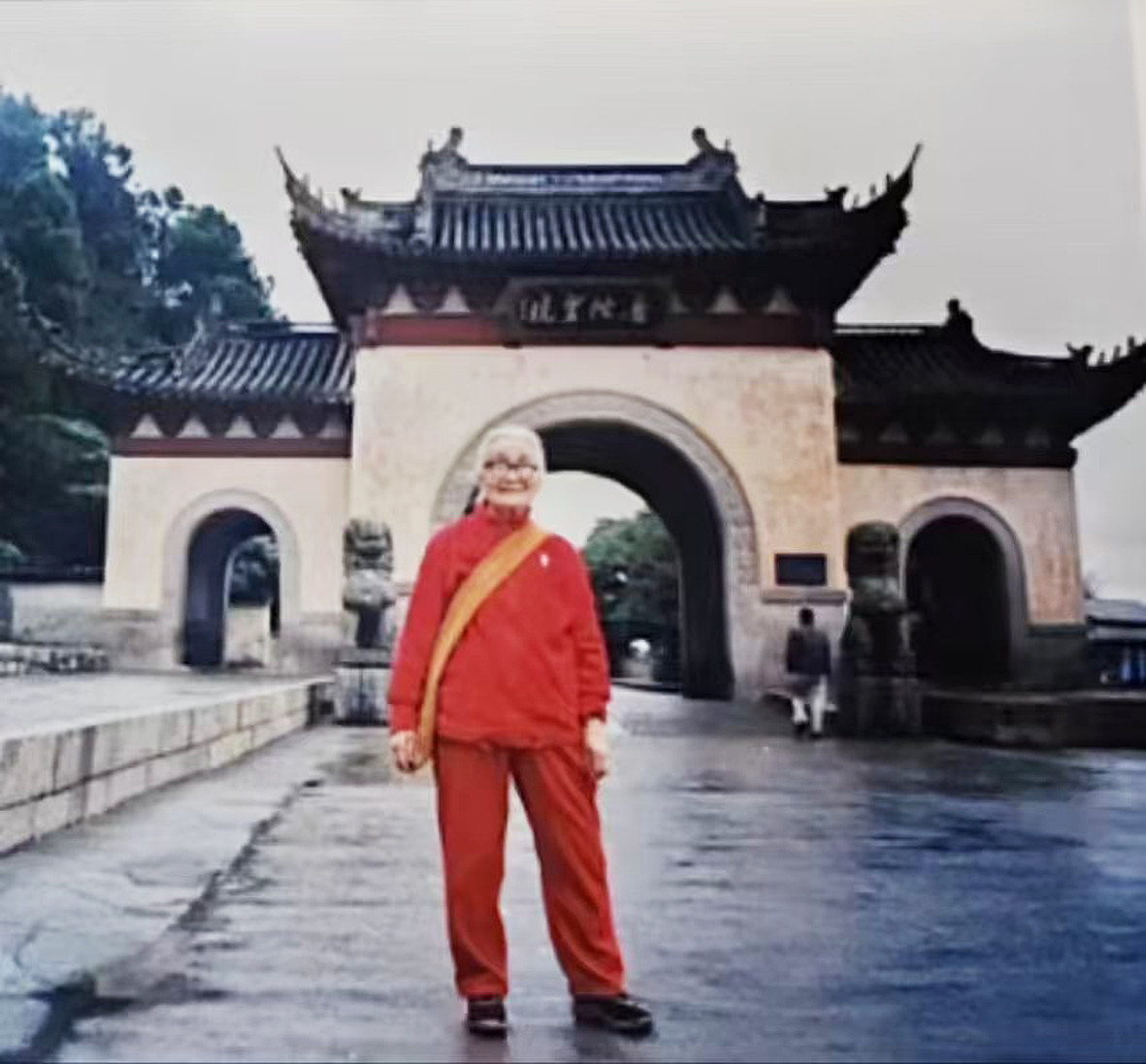
来到宁波余姚市梁弄镇的浙东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展柜中陈列的泛黄照片和人员名册时,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,连同照片中那个眼神清澈、带着稚气却无比坚定的少女身影,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——那竟是我的母亲孙礼清!一瞬间,历史的尘埃被拂去,时光的闸门轰然洞开。展厅里的灯光仿佛聚焦在那方寸之地,那个在官方叙事中被冠以“抗日小战士”称谓的身影,于我而言,是血脉相连的母亲,更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、充满荣光与坎坷的传奇人生的起点。
烽火中的早慧
母亲的革命生涯,始于一个战火纷飞、民族危亡的年代。1938年,她十九岁。在浙东四明山这片英雄的土地上,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,她毅然加入了余姚战时工作队。在敌后宣传动员社会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、团结一致奋起抗日,这不是一个孩童的游戏,而是需要直面血与火的考验。展柜里那张年轻的面庞,眼神里没有同龄人的懵懂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年龄的坚毅与使命感。
战时工作队的工作是宣传的号角,是凝聚民心的纽带。母亲的身影活跃在硝烟弥漫的乡村与山林间。歌咏传情,她清亮的嗓音在昏暗的油灯下、在田间地头,唱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,那些激昂的旋律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,更是点燃同胞心中抗日烈焰的火种。歌声穿透恐惧,传递着不屈的信念。面对惶恐或麻木的乡亲,她站上简易的土台,用铿锵有力的话语,揭露日寇暴行,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,号召大家团结起来。那份勇气,源自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光明的执着追求。
夜深人静时,她和战友们如暗夜精灵,将一张张印着抗日宣言、胜利消息的传单,巧妙地塞入门缝、贴在墙上。这些薄薄的纸片,是投向敌占区的精神炸弹,传递着希望和力量。她深入农户,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,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,组织妇女做军鞋、筹军粮,把最朴素的民众力量汇聚成抗日的洪流。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淬炼中,因其出色的表现和坚定的信仰,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不再是懵懂少女,而是一名肩负着民族解放使命的年轻战士,一颗扎根在四明山革命沃土中的红色种子。
离散与坚守
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,根据战略需要,主力部队奉命北撤转移至苏北。母亲,连同像她一样活跃在敌后的工作队员,大部分被留在了原地,继续坚持斗争或转入地下。她们是革命的星火,散落在广袤的敌后,期待着燎原之势的再次汇聚。
然而,历史的转折残酷而突然。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爆发,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,对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。白色恐怖笼罩浙东,为了保存革命力量,党组织紧急疏散人员,要求大家“隐蔽精干,长期埋伏,积蓄力量,以待时机”。母亲,这位年轻的党员,不得不含泪告别战斗过的土地和战友,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。她辗转躲避,最终流落到了当时被称为“孤岛”的上海。
在上海这个人海茫茫的都市,举目无亲,既要躲避无处不在的特务追捕,又要艰难谋生。她尝试过各种卑微的工作,尝尽了人间冷暖。她无数次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寻找组织,但严酷的环境和通讯的中断,如同厚重的铁幕,将她与曾经的革命集体彻底隔绝。那份寻找组织的焦灼、失去联系的彷徨与无助,是那段灰色岁月里最深的烙印。时光流逝,青春在等待与失望中蹉跎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为了生存,母亲最终不得不放下执念,像那个时代无数被命运抛离航线的普通人一样,选择了成家生子,过起了平凡的生活。然而,那颗革命的初心、那段峥嵘的岁月,始终是她心底最深的珍藏和最沉重的挂念。
曙光中的召唤
解放战争的炮声隆隆,1949年,新中国成立前夕,母亲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让她心跳几乎停止的名字——马青!那正是当年在四明山游击区时,她所在工作队的班长、区队长!报纸上关于他即将参与解放浙江、接管政权的消息,像一道划破漫漫长夜的曙光。没有丝毫犹豫,母亲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情,立刻提笔给这位老领导写信。她在信中详细诉说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,表达了对组织的思念和渴望归队的迫切心情。信寄出去了,带着她全部的希望。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,每一刻都充满了煎熬。
终于,回信来了!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让母亲的手微微颤抖。展开信纸,马青同志亲切而坚定的文字跃然纸上。他不仅清晰记得当年那个勇敢的小战士,更在信中明确指示:“欢迎归队!请速携家人回浙江参加革命工作!” 这寥寥数语,重逾千斤。它不仅是对母亲个人革命历史的认可,更是组织对一个离散多年的战士的深情召唤。信中,马青同志关切地询问母亲在上海是否有正式工作,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,他展现了一位老革命、新政权领导人的担当与关怀:“杭州、绍兴、宁波,三地可任意挑选!组织上没有忘记当年的小战士!” 这份信任与选择权,给予母亲最高的尊重和最温暖的抚慰。最终,父母亲选择了绍兴——这个江南水乡,作为他们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新起点。
归途中的暖流
在奔赴绍兴的途中,父母亲特意在杭州停留。消息不胫而走,一批当年在四明山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闻讯赶来。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二十多天啊!久别重逢,恍如隔世。白发已悄然爬上鬓角,皱纹刻下了岁月的风霜,但当年的战斗情谊却如陈年美酒,历久弥香。他们围坐在一起,追忆四明山的烽火岁月,讲述失散后的各自艰辛,畅谈新中国的美好前景。泪水与欢笑交织,感慨与豪情并存。这些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情谊,是革命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,也为母亲即将开始的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抵达绍兴,正值百废待兴、亟需干部的关键时刻。人才极度匮乏,对新干部的审查也极为严格。然而,母亲的情况极为特殊——她是在组织的直接召唤下,凭借当年老领导马青同志的亲笔信和证明,未经当时常规繁琐的组织审查程序而直接“重新入伍”的。这在当时严密的干部体系中,几乎是“绝无仅有”的特例。这背后,是马青同志对母亲当年表现的充分信任,是组织对那段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、虽被迫失联却从未变节的历史的尊重与认可。
母亲被委以重任,担任绍兴专员公署的政府机要秘书。这是一个极其关键且敏感的岗位,掌管着政府核心文件、机要通讯,责任重大,需要极高的政治可靠性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。父亲则被安排在财务部门工作,同样肩负重任。他们都享受着供给制,生活虽清贫,但精神无比充实,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建设新绍兴、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。上世纪50年代末,国家遭受3年的特殊困难,号召广大干部分担下放回乡生产,父母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回乡,并已把家具运到了余姚的外婆家,但是,被组织挽留召回,母亲不再在绍兴专员公署大机关工作,而是来到基层柯桥镇妇联任主任。为了生产自救,母亲从老家的余姚带来了许多能工巧匠带领广大妇女群众,办起了印染厂、纺织厂。如今来到柯桥轻纺城,看到世界一流的机器和最先进的纺织面料,这个杭州湾边上一个贫穷落后的乡镇变成了如今富饶活跃的城市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当年国家举全国之力建设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,父母也听从召唤,加入到支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。她在工程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,立足商贸阵地,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组织生活物资的供应,父亲则从省百货公司带领25个人的工作组来到建设工地,负责工程建设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采购、供应、管理工作,他们曾经数次荣获省级财贸先进工作者的殊荣。在新安江大街上,大家都亲热地称母亲为老班长,因为她曾经担任一批商店的负责人,最后母亲被派去整顿豆制品厂,带领大家把一盘散沙、工艺落后的工厂建成了半自动化流水线的先进企业。她常对我们说,有多少战友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有多少战友落下了伤残,有多少女战友经过长期的战斗生活,风餐露宿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,比起这些,她知足了。如此强烈的革命信念,鼓励她奋斗了一生。为了工作,他们常常废寝忘食,很少有时间回家。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养育和教育重任,几乎全部落在了具有“国高”(相当于高中)文化水平的奶奶身上。老人家深明大义,以她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文化素养和坚韧品格,悉心照料着孙辈的生活起居,督促学业。当然,作为长姐的大姐姐也早早承担起“小班长”的责任,帮助奶奶照顾弟弟妹妹。奶奶的付出和姐姐的担当,是支撑我们这个家庭在父母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最稳固的后方,这份恩情,我们兄弟姐妹永生难忘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