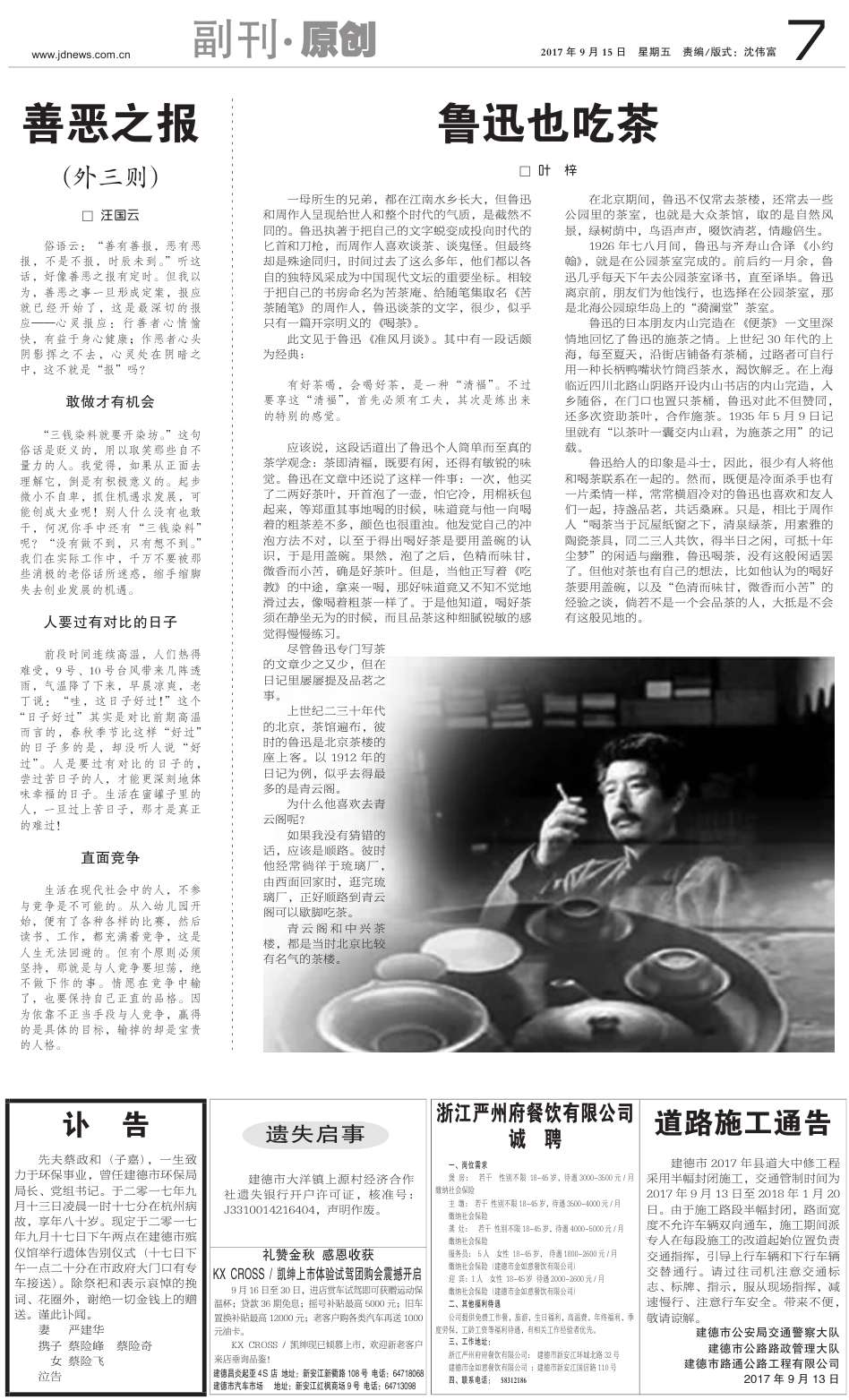еҶ…е®№иҜҰжғ…
2017е№ҙ09жңҲ15ж—Ҙ
йІҒиҝ…д№ҹеҗғиҢ¶
в–Ў еҸ¶ жў“
йҳ…иҜ»ж•°пјҡ1759 жң¬ж–Үеӯ—ж•°пјҡ1263
дёҖжҜҚжүҖз”ҹзҡ„е…„ејҹпјҢйғҪеңЁжұҹеҚ—ж°ҙд№Ўй•ҝеӨ§пјҢдҪҶйІҒиҝ…е’Ңе‘ЁдҪңдәәе‘ҲзҺ°з»ҷдё–дәәе’Ңж•ҙ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ж°”иҙЁпјҢжҳҜ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„гҖӮйІҒиҝ…жү§и‘—дәҺ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ж–Үеӯ—иң•еҸҳжҲҗжҠ•еҗ‘ж—¶д»Јзҡ„еҢ•йҰ–е’ҢеҲҖжһӘпјҢиҖҢе‘ЁдҪңдәәе–ңж¬ўи°ҲиҢ¶гҖҒи°Ҳй¬јжҖӘгҖӮдҪҶжңҖз»ҲеҚҙжҳҜж®ҠйҖ”еҗҢеҪ’пјҢж—¶й—ҙиҝҮеҺ»дәҶиҝҷд№ҲеӨҡе№ҙпјҢ他们йғҪд»Ҙеҗ„иҮӘзҡ„зӢ¬зү№йЈҺйҮҮ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зҺ°д»Јж–Үеқӣзҡ„йҮҚиҰҒеқҗж ҮгҖӮзӣёиҫғдәҺ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д№ҰжҲҝе‘ҪеҗҚдёәиӢҰиҢ¶еәөгҖҒз»ҷйҡҸ笔йӣҶеҸ–еҗҚгҖҠиӢҰиҢ¶йҡҸ笔гҖӢзҡ„е‘ЁдҪңдәәпјҢйІҒиҝ…и°ҲиҢ¶зҡ„ж–Үеӯ—пјҢеҫҲе°‘пјҢдјјд№ҺеҸӘжңүдёҖзҜҮејҖе®—жҳҺд№үзҡ„гҖҠе–қиҢ¶гҖӢгҖӮ
жӯӨж–Үи§ҒдәҺйІҒиҝ…гҖҠеҮҶйЈҺжңҲи°ҲгҖӢгҖӮе…¶дёӯжңүдёҖж®өиҜқйўҮдёәз»Ҹе…ёпјҡ
жңүеҘҪиҢ¶е–қпјҢдјҡе–қеҘҪиҢ¶пјҢжҳҜдёҖз§Қ“жё…зҰҸ”гҖӮдёҚиҝҮиҰҒдә«иҝҷ“жё…зҰҸ”пјҢйҰ–е…Ҳеҝ…йЎ»жңүе·ҘеӨ«пјҢе…¶ж¬ЎжҳҜз»ғеҮәжқҘзҡ„зү№еҲ«зҡ„ж„ҹи§үгҖӮ
еә”иҜҘиҜҙпјҢиҝҷж®өиҜқйҒ“еҮәдәҶйІҒиҝ…дёӘдәәз®ҖеҚ•иҖҢиҮізңҹзҡ„иҢ¶еӯҰи§ӮеҝөпјҡиҢ¶еҚіжё…зҰҸпјҢж—ўиҰҒжңүй—ІпјҢиҝҳеҫ—жңүж•Ҹй”җзҡ„е‘іи§үгҖӮйІҒиҝ…еңЁж–Үз« дёӯиҝҳиҜҙдәҶиҝҷж ·дёҖ件дәӢпјҡдёҖж¬ЎпјҢд»–д№°дәҶдәҢдёӨеҘҪиҢ¶еҸ¶пјҢејҖйҰ–жіЎдәҶдёҖеЈ¶пјҢжҖ•е®ғеҶ·пјҢз”ЁжЈүиў„еҢ…иө·жқҘпјҢзӯүйғ‘йҮҚе…¶дәӢең°е–қ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‘ійҒ“з«ҹдёҺд»–дёҖеҗ‘е–қзқҖзҡ„зІ—иҢ¶е·®дёҚеӨҡпјҢйўңиүІд№ҹеҫҲйҮҚжөҠгҖӮд»–еҸ‘и§үиҮӘе·ұзҡ„еҶІжіЎж–№жі•дёҚеҜ№пјҢд»ҘиҮідәҺеҫ—еҮәе–қеҘҪиҢ¶жҳҜиҰҒз”Ёзӣ–зў—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дәҺжҳҜз”Ёзӣ–зў—гҖӮжһң然пјҢжіЎдәҶд№ӢеҗҺпјҢиүІзІҫиҖҢе‘із”ҳпјҢеҫ®йҰҷиҖҢе°ҸиӢҰпјҢзЎ®жҳҜеҘҪиҢ¶еҸ¶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Ҫ“д»–жӯЈеҶҷзқҖгҖҠеҗғж•ҷгҖӢзҡ„дёӯйҖ”пјҢжӢҝжқҘдёҖе–қпјҢйӮЈеҘҪе‘ійҒ“з«ҹеҸҲдёҚзҹҘдёҚи§үең°ж»‘иҝҮеҺ»пјҢеғҸе–қзқҖзІ—иҢ¶дёҖж ·дәҶгҖӮдәҺжҳҜд»–зҹҘйҒ“пјҢе–қеҘҪиҢ¶йЎ»еңЁйқҷеқҗж— дёә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ҖҢдё”е“ҒиҢ¶иҝҷз§Қз»Ҷи…»й”җж•Ҹзҡ„ж„ҹи§үеҫ—ж…ўж…ўз»ғд№ гҖӮ
е°Ҫз®ЎйІҒиҝ…дё“й—ЁеҶҷиҢ¶зҡ„ж–Үз« е°‘д№ӢеҸҲе°‘пјҢдҪҶеңЁж—Ҙи®°йҮҢеұЎеұЎжҸҗеҸҠе“ҒиҢ—д№ӢдәӢгҖӮ
дёҠдё–зәӘдәҢдёүеҚҒе№ҙд»Јзҡ„еҢ—дә¬пјҢиҢ¶йҰҶйҒҚеёғпјҢеҪјж—¶зҡ„йІҒиҝ…жҳҜеҢ—дә¬иҢ¶жҘјзҡ„еә§дёҠе®ўгҖӮд»Ҙ1912е№ҙзҡ„ж—Ҙи®°дёәдҫӢпјҢдјјд№ҺеҺ»еҫ—жңҖеӨҡзҡ„жҳҜйқ’дә‘йҳҒгҖӮ
дёәд»Җд№Ҳд»–е–ңж¬ўеҺ»йқ’дә‘йҳҒе‘ўпјҹ
еҰӮжһңжҲ‘жІЎжңүзҢңй”ҷзҡ„иҜқпјҢеә”иҜҘжҳҜйЎәи·ҜгҖӮеҪјж—¶д»–з»ҸеёёеҫңеҫүдәҺзҗүз’ғеҺӮпјҢз”ұиҘҝйқўеӣһ家时пјҢйҖӣе®Ңзҗүз’ғеҺӮпјҢжӯЈеҘҪйЎәи·ҜеҲ°йқ’дә‘йҳҒеҸҜд»ҘжӯҮи„ҡеҗғиҢ¶гҖӮ
йқ’дә‘йҳҒе’Ңдёӯе…ҙиҢ¶жҘјпјҢйғҪжҳҜеҪ“ж—¶еҢ—дә¬жҜ”иҫғжңүеҗҚж°”зҡ„иҢ¶жҘјгҖӮ
еңЁеҢ—дә¬жңҹй—ҙпјҢйІҒиҝ…дёҚд»…еёёеҺ»иҢ¶жҘјпјҢиҝҳеёёеҺ»дёҖдәӣе…¬еӣӯйҮҢзҡ„иҢ¶е®Ө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еӨ§дј—иҢ¶йҰҶпјҢеҸ–зҡ„жҳҜиҮӘ然йЈҺжҷҜпјҢз»ҝж ‘иҚ«дёӯпјҢйёҹиҜӯеЈ°еЈ°пјҢе•ңйҘ®жё…иҢ—пјҢжғ…и¶ЈеҖҚз”ҹгҖӮ
1926е№ҙдёғе…«жңҲй—ҙпјҢйІҒиҝ…дёҺйҪҗеҜҝеұұеҗҲиҜ‘гҖҠе°ҸзәҰзҝ°гҖӢпјҢе°ұжҳҜеңЁе…¬еӣӯиҢ¶е®Өе®ҢжҲҗзҡ„гҖӮеүҚеҗҺзәҰдёҖжңҲдҪҷпјҢйІҒиҝ…еҮ д№ҺжҜҸеӨ©дёӢеҚҲеҺ»е…¬еӣӯиҢ¶е®ӨиҜ‘д№ҰпјҢзӣҙиҮіиҜ‘жҜ•гҖӮйІҒиҝ…зҰ»дә¬еүҚпјҢжңӢеҸӢ们дёәд»–йҘҜиЎҢпјҢд№ҹйҖүжӢ©еңЁе…¬еӣӯиҢ¶е®ӨпјҢйӮЈжҳҜеҢ—жө·е…¬еӣӯзҗјеҚҺеІӣдёҠзҡ„“жјӘжҫңе Ӯ”иҢ¶е®ӨгҖӮ
йІҒиҝ…зҡ„ж—Ҙжң¬жңӢеҸӢеҶ…еұұе®ҢйҖ еңЁгҖҠдҫҝиҢ¶гҖӢдёҖж–ҮйҮҢж·ұжғ…ең°еӣһеҝҶдәҶйІҒиҝ…зҡ„ж–ҪиҢ¶д№Ӣжғ…гҖӮдёҠдё–зәӘ30е№ҙд»Јзҡ„дёҠжө·пјҢжҜҸиҮіеӨҸеӨ©пјҢжІҝиЎ—еә—й“әеӨҮжңүиҢ¶жЎ¶пјҢиҝҮи·ҜиҖ…еҸҜиҮӘиЎҢз”ЁдёҖз§Қй•ҝжҹ„йёӯеҳҙзҠ¶з«№зӯ’иҲҖиҢ¶ж°ҙпјҢжёҙйҘ®и§Јд№ҸгҖӮеңЁдёҠжө·дёҙиҝ‘еӣӣе·қеҢ—и·Ҝеұұйҳҙи·ҜејҖи®ҫеҶ…еұұд№Ұеә—зҡ„еҶ…еұұе®ҢйҖ пјҢе…Ҙд№ЎйҡҸдҝ—пјҢеңЁй—ЁеҸЈд№ҹзҪ®еҸӘиҢ¶жЎ¶пјҢйІҒиҝ…еҜ№жӯӨдёҚдҪҶиөһеҗҢпјҢиҝҳеӨҡж¬Ўиө„еҠ©иҢ¶еҸ¶пјҢеҗҲдҪңж–ҪиҢ¶гҖӮ1935е№ҙ5жңҲ9ж—Ҙи®°йҮҢе°ұжңү“д»ҘиҢ¶еҸ¶дёҖеӣҠдәӨеҶ…еұұеҗӣпјҢдёәж–ҪиҢ¶д№Ӣз”Ё”зҡ„и®°иҪҪгҖӮ
йІҒиҝ…з»ҷдәәзҡ„еҚ°иұЎжҳҜж–—еЈ«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ҫҲе°‘жңүдәәе°Ҷд»–е’Ңе–қиҢ¶иҒ”зі»еңЁдёҖиө·зҡ„гҖӮ然иҖҢпјҢж—ўдҫҝжҳҜеҶ·йқўжқҖжүӢд№ҹжңүдёҖзүҮжҹ”жғ…дёҖж ·пјҢеёёеёёжЁӘзңүеҶ·еҜ№зҡ„йІҒиҝ…д№ҹе–ңж¬ўе’ҢеҸӢдәә们дёҖиө·пјҢжҢҒзӣҸе“ҒиҢ—пјҢе…ұиҜқжЎ‘йә»гҖӮеҸӘжҳҜпјҢзӣёжҜ”дәҺе‘ЁдҪңдәә“е–қиҢ¶еҪ“дәҺз“ҰеұӢзәёзӘ—д№ӢдёӢпјҢжё…жіүз»ҝиҢ¶пјҢз”Ёзҙ йӣ…зҡ„йҷ¶з“·иҢ¶е…·пјҢеҗҢдәҢдёүдәәе…ұйҘ®пјҢеҫ—еҚҠж—Ҙд№Ӣй—ІпјҢеҸҜжҠөеҚҒе№ҙе°ҳжўҰ”зҡ„й—ІйҖӮдёҺе№Ҫйӣ…пјҢйІҒиҝ…е–қиҢ¶пјҢжІЎжңүиҝҷиҲ¬й—ІйҖӮзҪўдәҶгҖӮдҪҶд»–еҜ№иҢ¶д№ҹ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жғіжі•пјҢжҜ”еҰӮд»–и®Өдёәзҡ„е–қеҘҪиҢ¶иҰҒз”Ёзӣ–зў—пјҢд»ҘеҸҠ“иүІжё…иҖҢе‘із”ҳпјҢеҫ®йҰҷиҖҢе°ҸиӢҰ”зҡ„з»ҸйӘҢд№Ӣи°ҲпјҢеҖҳиӢҘ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дјҡе“ҒиҢ¶зҡ„дәәпјҢеӨ§жҠөжҳҜдёҚдјҡжңүиҝҷиҲ¬и§Ғең°зҡ„гҖӮ